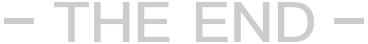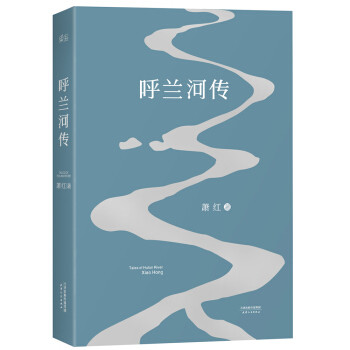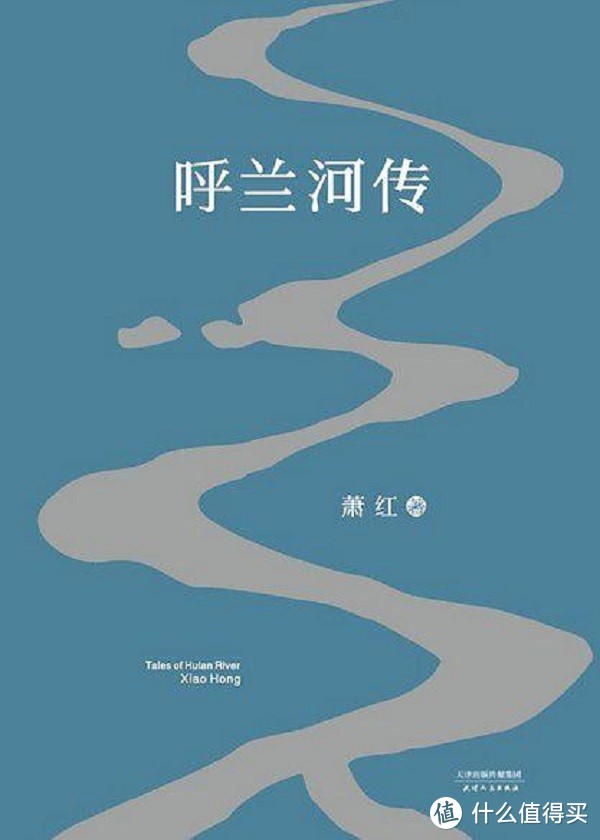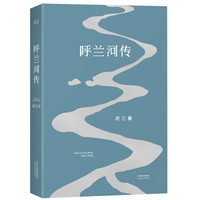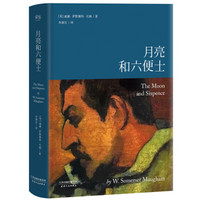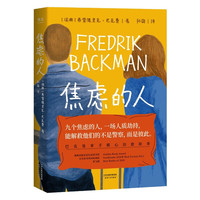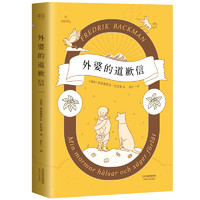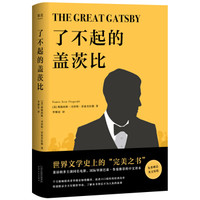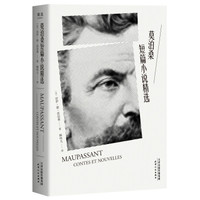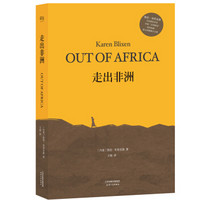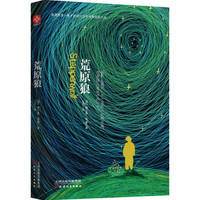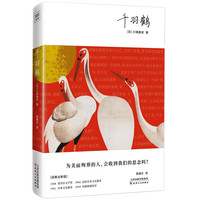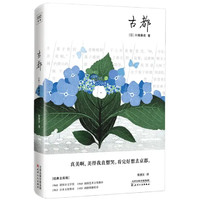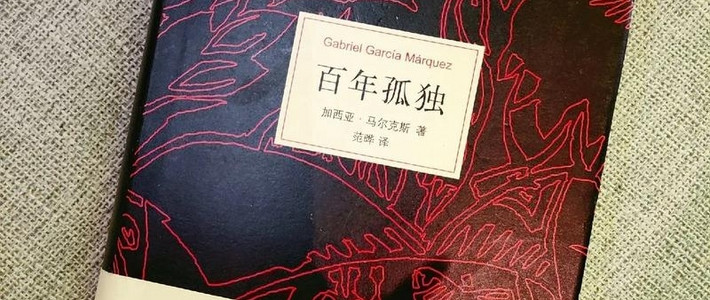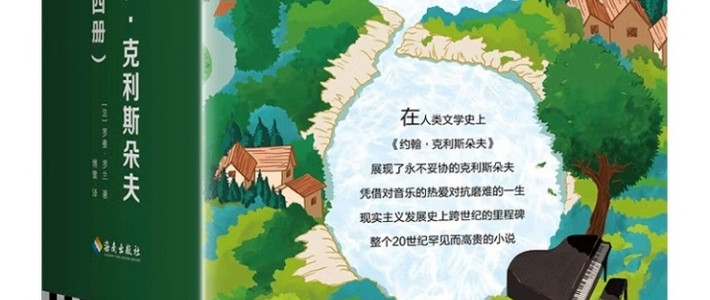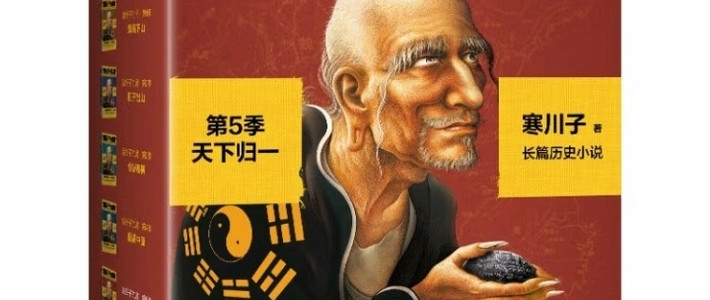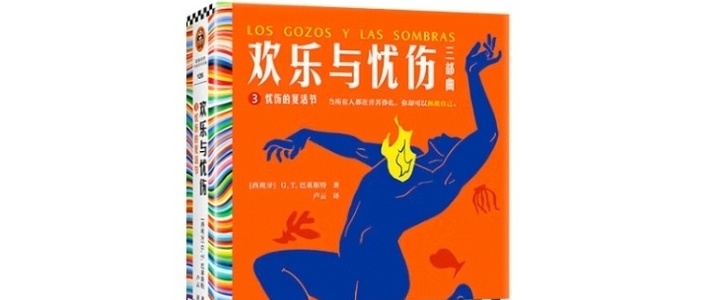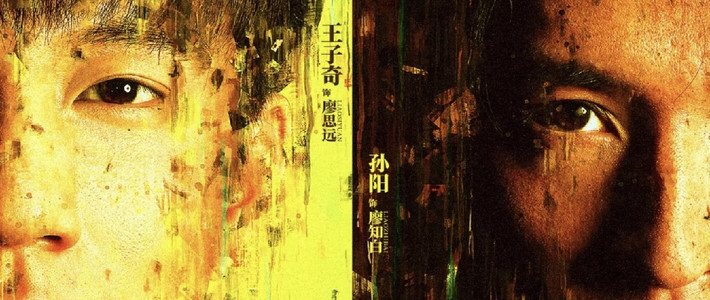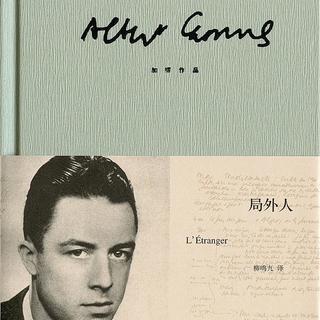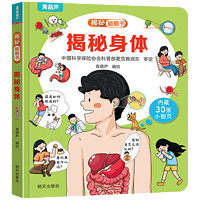中国当代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,我说是她你认么?
01读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,第一印象是:这姑娘太可爱了!
作品以儿童视角展开叙述,我们读到的是一个很天真很稚嫩的口吻,在饶有趣味地讲述着家乡呼兰河的一切。
在这种视角下,好像呼兰河什么都是可爱的,连寒冷的天气,也被叙述成“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,哽哽的,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了一样”式的顽皮童趣。
呼兰河是一个不怎么繁华的小城,城里只有两条大街。然而就是这样的小城,却被萧红描绘得生动无比。
她谈到呼兰河的人,什么都讲结实耐用。比如是药膏,虽然是贴了半个月,手也还没有见好,但这膏药总算是耐用,那就算是没有白花钱。小城有它的好处,亲密,热闹,和气,有人情味,同时也有它的坏处,譬如总爱占便宜的人们,飞个不停的流言,以及躲不开的各种家长里短。
小说里“团圆媳妇”洗澡的情节尤其让人难忘。
为了用偏方治团圆媳妇的病,婆婆将她剥光衣服,按到滚热的水中去,在大庭广众之下“洗澡”。当时的呼兰河还没有报纸,以至于“不能记录这桩盛事”。而那些瘫痪的人,没能看到这样的“盛事”,简直算的上事“一生的不幸”。
本来是戏谑幽默的语气,但语气下暴露出的事实是残酷的,读来是让人心碎的。只不过呼兰河的众人没能够意识到这一点,依旧是热热闹闹地去看赤裸的团圆媳妇洗澡。
读到后来,会觉得这种口吻虽然童稚,却同时有着圣经般的庄严。
比如在书中,叙述者问道,“节妇坊上为什么没写着赞美女子跳井跳得勇敢的赞词?”问完之后,又答道,“那是修节妇坊的人故意给删去的。因为修节妇坊的,多半是男人。他家里也有一个女人。他怕是写上了,将来他打他女人的时候,他的女人也去跳井。女人也跳了井,留下来一大群孩子可怎么办?于是一律不写。只写,温文尔雅,孝顺公婆……”
正所谓童言无忌,正是这种无忌的童言,让真相如此刺人,却又如此不着痕迹。
但偏偏童言最不会浅尝辄止,它会顺着人们通常的禁忌话题不停地追问下去。
譬如看到泥像,又会问“那么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他塑成那个样子呢?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,不但磕头,而且要心服。就是磕完了头站起再看着,也绝不会后悔,不会后悔这头是向一个平庸无奇的人白白磕了。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,那就告诉人,温顺的就是老实的,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,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。”
这语气让讽刺都显得温和了起来,让人想起钱钟书那句“忠厚老实人的恶毒,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,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”,读《呼兰河传》也是这样,在童稚天真的笔触下,实际上隐藏着令人心碎的人生片段,同样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。
乍一读来,它好像是很随意的,很散漫的。
细细看下去,发现它又是很讽刺的,很深刻的。
这正是萧红在《呼兰河传》中书写的最大特点。
02
如果在古代,萧红该是位顶好的诗人。
《呼兰河传》中常常能读到让人心旷神怡的句子。
刚开始,写呼兰河的天气时,她这样写道: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,一切都变了样,天空是灰色的,好像刮了大风之后,呈着一种混沌沌的气象,而且整天飞着清雪。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,嘴里边的呼吸,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。
连贯的短句,准确的用词,让人很快沉浸在寒冷的呼兰河中去了。
又比如这段:
满天星光,满屋月亮,人生何似,为什么这么悲凉。
灯光照得河水幽幽的发亮。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。真是人生何世,会有这样好的景况。
读来真是让人感叹不已,我觉得用“散文诗一样的小说”来形容它更为贴切。
萧红似乎就是有这样与生俱来对文字的敏感,能够迅速地捕捉到近乎直觉一样的词语和氛围,运用恰到好处的文字将其摹写下来,一点便触及到了事物的“精魂”。
当这种诗意与童稚的特点结合在一起之后,便成了趣味盎然的童诗式小说。
“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,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。祖父戴一个大草帽,我戴一个小草帽,祖父栽花,我就栽花,祖父拔草,我就拔草。”
这一段让人想起诗人朱湘在《草莽集》中的一首《采莲曲》,"左行,右撑"、"拍紧,拍松",便是用先重后轻的声韵与文字搭配,表现出小舟在采莲时,不断向前划动,小舟上下浮动的一种感觉。
但萧红和朱湘又有着不同。诗人的雕琢是必然的,而小说家的诗意则更像是神来之笔。萧红给人一种不费功夫就信手拈来的轻松感,同时又具有悠长的余韵在字里行间。
写祖父的后花园,最精彩的要数这一段:
花开了,就像花睡醒了似的。鸟飞了,就像鸟上天了似的。虫子叫了,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。一切都活了。都有无限的本领,要做什么,就做什么。要怎么样,就怎么样。都是自由的。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,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。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,就开一个谎花,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。若都不愿意,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,一朵花也不开,也没有人问它似的。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,他若愿意长上天去,也没有人管。蝴蝶随意的飞,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,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。它们是从谁家来的,又飞到谁家去?太阳也不知道这个。
这是萧红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人生观,也是她借花鸟之口所表达出最理想的人生状态。
这种信手拈来的感觉同样体现在情景刻画上。
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,写看热闹的人群:
这过路的人分成两种,一种是穿着长袍短褂的,非常清洁。看那样子也伸不出手来,因为他的手也是很洁净的。不用说那就是绅士一流的人物了,他们是站在一旁参观的。看那马要站起来了,他们就喝彩,“噢!噢!”的喊叫着,看那马又站不起来,又倒下去了,这时他们又是喝彩,“噢噢”的又叫了几声。不过这喝的是倒彩。
这种“看-被看”的情景模式是常常出现在鲁迅小说中的经典情景。
小说最妙的是,看似处处是闲笔,但处处值得玩味,值得思索,值得解读。
有点散文的感觉,读来似乎行文散漫,实际上章篇结构非常清晰,譬如第一章写琐碎生活勾勒大致轮廓,接着写盛典就是浓墨重彩。
也不愧鲁迅评价萧红是“中国当代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”了。
萧红,我心目中真正的文学天才。
3之前我写过一篇关于《生死场》的书评。
在《生死场》中,人们像动物一样找寻着食物,贪婪地寻找着一丁点利益,让自己活得舒服一点,再舒服一点,然后忙着娶妻,忙着生子,再忙着寻生计。当物质极度匮乏的时候,人的尊严荡然无存。人们既体会不到自己的灵魂,也感受不到任何爱和温情。正如萧红写道,农家无论是菜棵,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。
和《生死场》的沉重相比,《呼兰河传》显然多了几分温柔和轻盈。
人间总是苦涩的,但作家的笔触在此时悄悄收起了锋利。
倘若仔细思考起来,呼兰河人也在过着一种茫然的,无知的生活。
“天黑了就睡觉,天亮了就起来工作。一年四季,春暖花开,秋雨,冬雪,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,脱下单衣去的过着。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的默默的办理。”
生活中也许会有巨大的痛苦与悲哀,比如卖豆芽菜的女疯子,虽然已经疯了,仍忘不了悲哀,“隔三差五的还到庙台上去哭一场,但是一哭完了,仍是得回家去吃饭,睡觉,卖豆芽菜。”
这种平静的悲哀和《生死场》中的悲哀有异曲同工之妙,只不过更使人感到一种平凡的凄凉,以及这世界秩序的不可动摇来。
日子是很苦的,只是稀里糊涂的苦,好像忍受这种苦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。
“生,老,病,死,都没有什么表示。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,长大就长大,长不大也就算了。老,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。眼花了,就不看;耳聋了,就不听;牙掉了,就整吞;走不动了,就瘫着。这有什么办法,谁老谁活该。”
咬着牙,痛苦与欢乐,忧愁与幸福,都在飞逝的日子中溜走了,并没什么特别之处。
“春夏秋冬,一年四季来回循环的走,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。风霜雨雪,受得住的就过去了,受不住的,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。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,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。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,就风霜雨雪,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。”
从这个角度来看,呼兰河像是一座停滞的小城。因为这里的人们不关注过去,也不关注未来,只是专注地盯着现在,全心全意地生活在当下。或许这是一种非凡的乐观,也可以说是一种别样的麻木。
庸庸碌碌,迷迷茫茫地度过这一生。
便是呼兰河人们的常态。
又何尝不是世上大多数人的常态呢?
摹写了如此的呼兰河图景后,萧红也在书中给出了自己对于人生的解读,是“随意”二字。
“你说我的生命可惜,我自己却不在乎。你看着很危险,我却自己以为得意。不得意怎么样?人生是苦多乐少。”
这确实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与麻木,可又何尝不是一种潇洒的豁达呢?
我倒是私以为,这种随意与豁达,是萧红最最可爱的地方了。